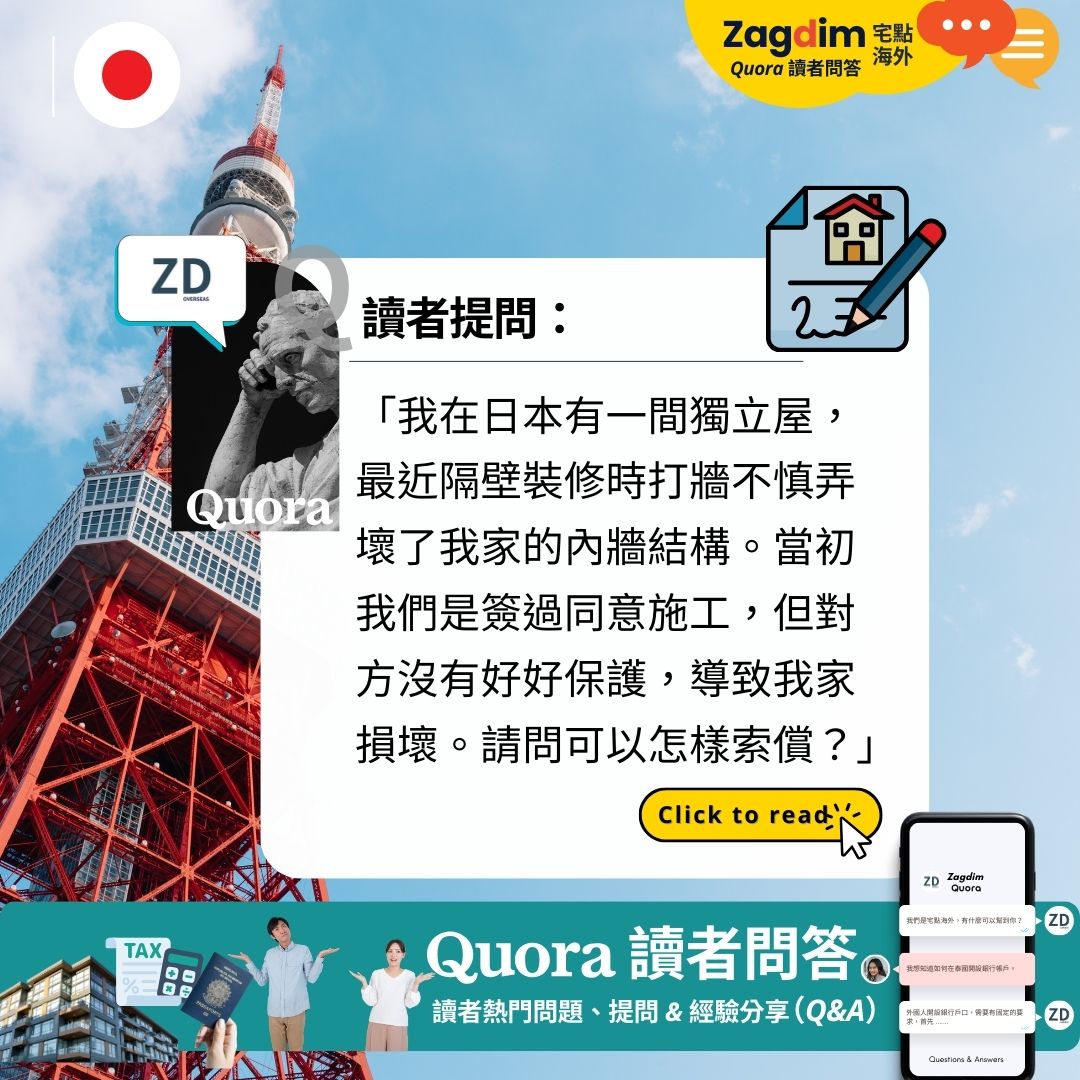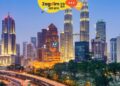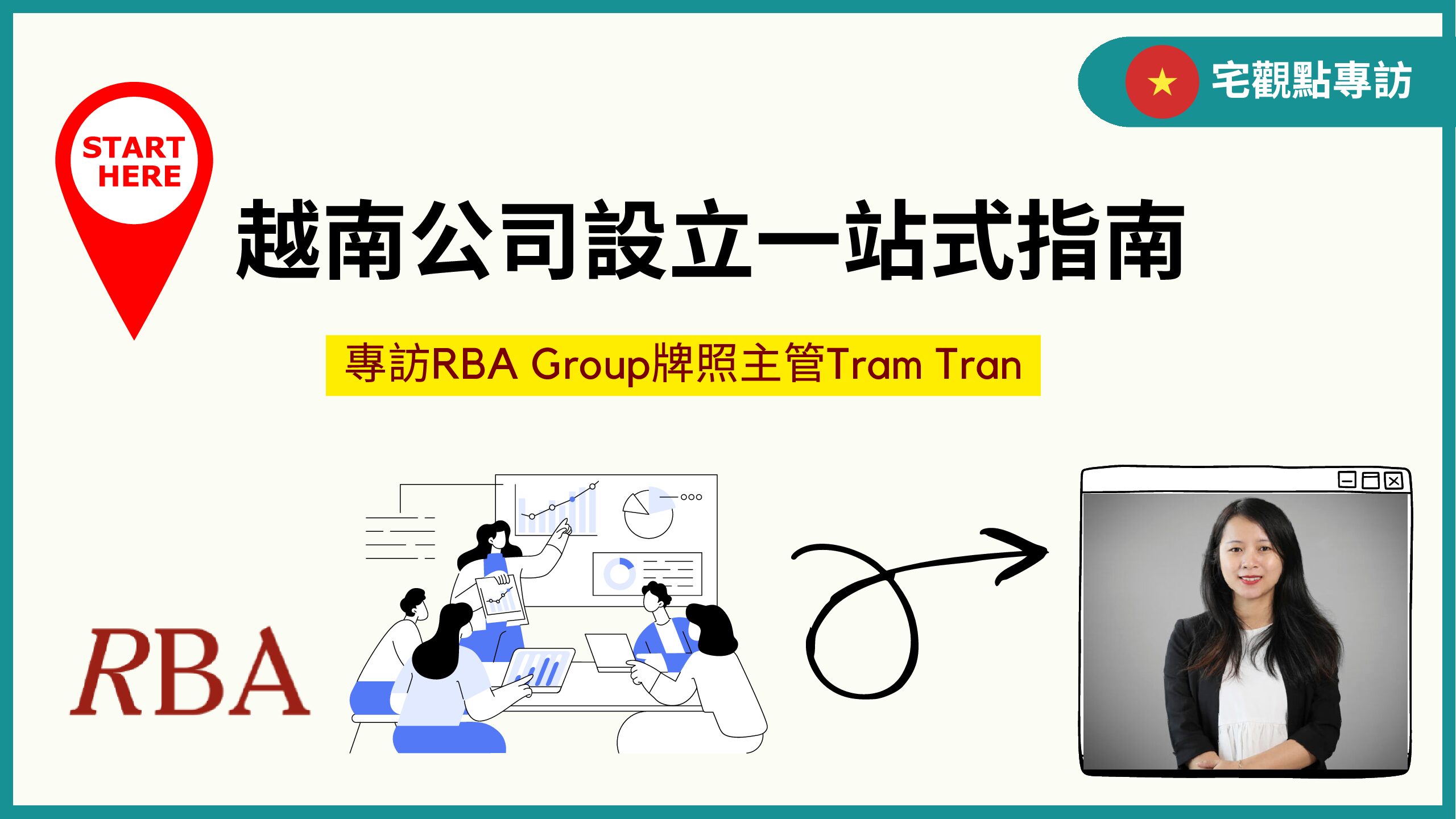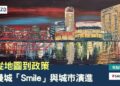為何巴里島幾乎沒有吉鋪?因為每間屋,都住了一個 John Dutton
最近待在巴里島,一件小事讓我越來越好奇:為什麼這裡的店舖,即使不是旅遊旺季,街上遊客稀少、景氣也沒特別好,可路邊的雜貨店、摩托維修站、賣椰子水的小亭子,甚至那家看起來三天沒客人的按摩店——都還開著,幾乎沒有吉鋪。
這讓我想到之前住在清邁時的場景:尼曼區疫情後簡直像一場資本撤退現場,整條街關了一半。

我開始問自己——到底差在哪?
起初我以為是「租金便宜」,但深入了解才知道:在巴里島,很多這些店鋪根本不是租來的,而是直接在自己家門口搭起來的。
不少家庭的土地是祖傳的家族地,加個棚子、擺張桌子,就能開起 warung(小食堂)或民宿。所以即使收入不好,只要電費和飯錢打得平,還有事情做、有面子掛著招牌,就會繼續營業。這種生活邏輯,和清邁那種「資本做生意 → 沒利潤就撤」的模式完全不同。
但從歷史來看,巴里島原本就是一個,宗族村社制 × 印度教信仰 × 自給型農業交織的島嶼。多數是透過村落或家族繼承方式保留,令土地不能輕易買賣。若拜訪巴里島任何一戶家庭,很可能會看到:住屋、家廟、稻田,甚至一間手工藝小店,都在同一塊地上。那不是刻意規劃出來的,而是生活自然長出來的樣子。
更有趣的是,這種模式從未被殖民或政府徹底打散。連荷蘭殖民時期都沒有完全破壞巴里島的土地共管與宗教分層制度;後來印尼政府也承認了「Subak(農業灌溉組織)」這套村社系統,直到今天仍在運作。根據文化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的著作《Negara: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-Century Bali》中的觀察:
「峇里島的政治與社會秩序,並非僅僅是行政或經濟組織,而是一場由宗教儀式構築的展演體系。」「家族 × 宗教 × 農地」**組成了整個身份認同的邏輯核心。

雖然今日不再是抵抗殖民的時代,但這樣的文化傳統,讓家庭仍保有小塊稻田——平時可能出租,或交由村人耕作;自己則偶爾參與,或在祭典時回鄉幫忙。那不只是農事,更是一種與祖靈、村落、祭祀之間的深層聯繫。
這樣的環境,我想起在飛機上,在看 Yellowstone 時 John Dutton 說的:
“Leverage is knowing that if someone had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, this ranch is what they’d buy.”
作為流動著資本主義血液的物業分析作者,眼中看著旅遊區黃金地段,腦中不斷閃過人流數據、消費力、未來回報,但眼看到,家家戶戶或是每隔一百米就設有家族的寺廟,祖傳的家族地這傳統。
資本與傳統的平衡,在這裡有自己獨特的模式。